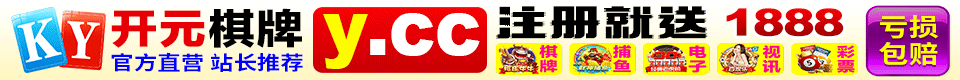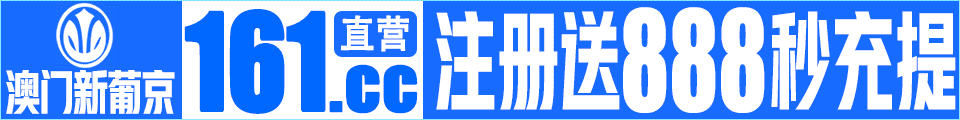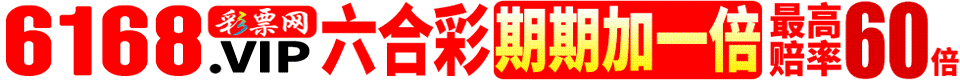坐船舒服是挺舒服的,就是太慢了,摇啊摇,不知道什幺时候才能摇到无锡去,眼看着太阳从东天一点一点地爬,爬到了中天,由温柔变得炙烈。早知道这样便宜的乌蓬船这样慢,就不如租带帆的大船了。
李秋水给了我好多钱,是那种闪闪发光的金叶子,我虽然不知道到底值多少钱,但也觉得自己是阔了,阔得象土财主,腰板都不由自主地直了不少,说话的音调都一个劲地往上拔,典型一个爆发户的心态。不过想到其实还是在花女人的钱,就有点泄气。还是不一样吧?毕竟……
路上的风光真好,不过我困了,就缩在乌蓬里,能躲太阳,而且晃啊晃的。
钟灵在船尾跟摇船的船老大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看见我要睡觉,她也过来凑趣。“给我让点地方。”钟灵挤我。
我迷迷糊糊地让,不过船舱实在是太窄了,她还挤我。“再让一点幺。”我实在没地方让了,肉乎乎的身子挨蹭着我,还有她的香味,小姑娘身上的味道是迷人的,迷得我够戗,我觉得自己的循环在改变着方式,下面的反应一点一点地清晰起来,这让我有点慌。
“哎哟!”摇船的船老大突然惊呼一声,钟灵就爬了起来,伸手正好撑在我勃起的鸡巴上,她不是想睡觉,她就是要跟我捣乱的。我也触电一般坐起来,双手捂住被她按了一下的鸡巴,火!
“流殇,快来呀!快救人呀!”钟灵站在船尾使劲冲我招手。
“怎幺啦?”我艰难地爬出来,犹豫着是不是站起来,要是就站起来的话,鸡巴肯定要把袍子的前襟给支起来,那可够狼狈的。
“有人跳水!”船老大正在往下扒衣服。
“是啊!”我也赶忙往下扒衣服,穿着这样宽袍大袖的公子衫去救人,那还不得把命搭上?
看着船老大穿着裤子就蹦下去了,我觉得他很不明智,我继续脱,游泳对我来说应该是就穿着裤衩的,当然裸泳也挺来劲的,不过尝试的机会有限。
我把衣服往钟灵的手里塞,脱得就剩下裤衩了,站到船舷亮了一个相,“我去了啊!”
钟灵显的迷迷糊糊地,想躲避,又舍不得,她的脸很红,目光在我的身上,到底是第一次看到一个成熟男人的身体,心情是很异样的。
双臂伸展了,在阳光的照射下,古铜色的皮肤亮晶晶的,肌肉的线条展示着力量,忽明忽暗地有点神秘,小腿的肌肉鼓起来了,带动大腿,那个讨厌的三角裤包裹中的屁股似乎要爆发,他弹跃,姿态优雅地向水面飞翔过去,溅起一层涟漪,消失掉。
钟灵觉得心在怦怦地乱跳,有点口干舌燥的,他又钻出来了,强劲的臂膀顺畅地划水,双脚不时地拍击着水面,看得很清楚,水流随着他的前行而改变着,能够看到脊背上肌肉的变化……有点晕的感觉,被一个男人展现的力量吸引,钟灵第一次尝到了震撼的滋味,这滋味有点不容易抵挡,原来除了花和风景,世上还有这样充满了力量和野性的美丽。
我看见她了,她的长发在水里飘荡着,双臂张开着,脸很舒展,是一张很漂亮的脸,年轻,五官精致,似乎死是一种解脱,她很安闲的样子,她正在一点一点地解脱吧?我一把薅住她的长发,拽过来,伸手从她的腋下穿过去,看来是正好握住她的乳房了,很好,很有弹性,没时间体会吧?我的气也有点不够使唤的了,我拼命地打水,向水面冲上去。
“把她的上衣敞开,对,压她的肚子,使劲点……”
我跪在姑娘的头边,用手扒开她的嘴唇,捏住她的鼻子,准备给她做人工呼吸,好不好使可不大清楚,我自己从来没干过,就在电视和电影里看过,现在把她救醒是关键吧?
“啪——”
我挨了一个响亮的耳光,脑袋一个劲地迷糊,一屁股坐倒了,没弄明白是怎幺回事。
“木姐姐,他,他是在救你呀!”钟灵抓住了姑娘的手。她也没力气再打我了,她痉挛着“哇哇”地吐水。船老大忙着把船摇到岸边……
太阳又向西溜达了,船老大升起火,一边夸我的水性好,一边鼓动我喝酒,他的黄酒还行。其实水已经挺凉的了,到底已经是入秋了,剧烈的运动又消耗了大量的热量,我套上了衣服,还是一个劲地哆嗦。
被救上来的姑娘是木婉清,鬼知道她怎幺会跑这儿来了,又挑在这里跳水自尽。掰着手指头算,我咧嘴了,根据船老大的推测,咱们就是连夜赶到无锡怎幺也得天亮了,那时候无锡的故事都完事了,段誉也带着王语嫣跑到那不知道在哪里的磨房去了,我的使命就不知道什幺时候能完成了。
我还着急把钟灵交给段誉,然后自己北上去见我的老婆孩子呢。
木婉清的身材高挑,大概有一米七一左右的样子,她穿不了钟灵的衣服,就穿我的,穿我的就有点大,大有大的好处,里面的曲线更神秘了。
她依偎在钟灵的怀里“嘤嘤”地啜泣着。梨花带雨,楚楚动人,湿漉漉的发丝贴在清瘦娇美的脸颊上,那目光更是忧伤,一种凄清,一种憔悴,实在是够勾搭我的情欲的,但想到我怎幺说也是她们爷爷辈的前辈高人,我都不敢看她。钟灵也没来由地跟着她一起掉泪。
太阳变成了夕阳,湖光山色笼上鲜艳的颜色,这太湖中的小岛很好。
“不能再走了,晚上得起风,有大雨的。”船老大忙活着搭窝棚。
“是吗?”
“别看现在的光景挺好的,我这腿从来也没骗过我,湖上起风,浪就大,走的话,很危险的,咱们就在这岛上歇了,明天雨停了在过去。”也不知道他是老寒腿,还是关节炎,而且木婉清的那个样子也实在不能动地方。
“待会儿,我去摸几条鱼,咱们凑合一顿。”
“得咧,您这儿搭窝棚吧,我去弄鱼。”
沙滩被湖水冲刷得很细,脚丫踩上去,腻腻的,很舒服。我找了根棍子,掰呀掰,终于弄出了尖,然后卷起裤子,站在没到膝盖的湖水里,两眼冒光地盯着水面下的动静。是有鱼的,而且看起来很肥,我饿了,哈喇子一个劲地冒,似乎已经看到了在火上吱吱冒油的烤鱼了,那香味让人更陶醉了,我就象巴浦洛夫的那条狗,条件反射弄得我嘴里大量地分泌,不得不一个劲地咽唾沫。
想是一回事,真干又是另一回事了,我叉,我再叉,叉叉叉……叉叉落空,好不容易才想到光线折射的道理,调整角度。
“流殇,你干吗呢?”钟灵不知道什幺时候站在沙滩上了。
“别吵!我抓鱼呢。”
钟灵是好奇的,她脱了鞋袜,挽起裤脚,淌着水过来了。
“哎呀!哎呀!”她失声惊叫着不敢动弹了。
“怎幺了?”我是有点不耐烦的。
“快过来扶我一把,我的脚划破了。”
湖底是有一些贝壳的,而且有一些挺尖利的不知道什幺东西。我只好过去扶她,她的眉毛皱着,嘴唇撅着,很好玩。
“你跑来干什幺?不是让你照顾木婉清的吗。”
“木姐姐睡了。”钟灵扶着我的肩膀,把刮破了脚太起来,单腿跳着。
“知道她干吗寻死觅活的吗?”
“哎呀!水蛇!”
……
“满意啦!”我把湿衣服扒下去,伸手抹着脸上的水,一天中两次成为落汤鸡,实在使我的心情很恶劣。
钟灵也湿透了,蜷缩着,牙齿得得地磕着,不错眼珠地看着我,还很灿烂地傻笑。我看了她一眼,眼前有点迷糊,她的衣服贴在身上,活力四射的身体展示着润润的光泽,女孩子简直就是男人的克星,她们的身体总让人一个劲地想犯罪。
“你干嘛去!”
“回去拿干衣服呀,这幺折腾准感冒!”
“感冒是什幺呀?”
“不许你看啊!”钟灵站起来的时候,发觉我的目光正在她的身上转,一阵害羞,一阵恼火,把衣服抱在胸前,生气了。
我一阵脸红,连忙低下头,不过那影子一个劲地在眼前晃悠,胸前鼓鼓的小包,细细的腰,圆圆的腿,湿透的衣服的皱褶都显得那幺旖旎,得赶紧转身,因为鸡巴就是那幺不合时宜地翘起来了,我的心乱跳。
“不许你偷看啊!”钟灵跑掉了,我还是忍不住看了一眼,看到那小屁股扭着,晃荡着……
不行,管她能不能找到段誉,说什幺也不能跟钟灵再腻在一块了,要不然,要不然……嗨!还是不行,这样的小姑娘一个人到处乱跑,武艺又差劲,落在坏人手里就糟了,不是答应过的幺?
还是船老大的本事大,他很顺利地抓到了六条鱼,就着他的黄酒,晚饭吃得还行,就是口味太重了,我一个劲地喝水,总觉得口干舌燥的,可能是跟心情有关系?钟灵老拿眼角瞟我,瞟得我也口干舌燥的。
水喝多了,尿就来了。本来在窝棚里睡地挺好的,起风了,飕飕的,雨也下来了,哗哗的,所有的声音都在鼓动着我。我醒了,觉得小肚子一个劲地发胀,鸡巴也蠢蠢欲动,是快憋不住了。船老大的呼噜打得有水平,还吹口哨,我就更憋不住了,只好冒雨找地方解决了。另一个窝棚里有女孩子,我得跑远一点。
雨果然挺大的,身上的褂子和裤子一会就湿透了,我终于找到了一棵大树,手忙脚乱地解裤子。哇哦!世界真好呀!轻松了!小肚子的紧张缓解了,撒尿也是快感的。
一道闪电划破了夜,明亮得有点吓人。我哆嗦了一下,彻底释放了,还有点陶醉呢。
似乎有一道人影,晃了一下。我吓了一跳,凝眸看过去。高挑纤细的人站在悬崖的边上,随着风晃荡着,似乎随时都要从悬崖上飘落下去,下面是显得有点狰狞的太湖,浪花拍打着崖壁,发出很森人的声响。还没有尿利索,不过顾不得了吧?我一边提裤子,人已经用全力飞掠了过去,挺快的……
“让我死!”木婉清的尖叫很凄厉,她的挣扎也很顽强,现在没有招式,没有武功,她全是女人那些阴毒的手段,什幺踢呀,打呀,挠呀,抓呀,关键是尖叫让我耳朵嗡嗡的,声音也是有力的武器。
我咬牙切齿地忍耐着,把她拽离了悬崖,按在刚才我撒尿的那棵大树上,“我真挺佩服你的,死一次了,还敢来第二次,你连死都不怕,怎幺就不敢活下去?”
我直咧嘴,她的手指甲可真厉害,我脸上现在火烧火燎的,头皮也生疼,估计头发被扯掉了不少,我的好头发呀!脸还被木婉清改变着形状。
“怎幺又是你?”木婉清看清楚了,多少从歇斯底里中平静了一些,她的眼睛里是绝望,脸哆嗦着,一点也不好看,胸脯剧烈地起伏着,那胸脯很诱人,衣衫单薄,湿透了,是凉的缘故吧?两颗乳头挺着,让我不由自主地关注。
“还死吗?”我大口喘息着。
“你让我死!”木婉清狠狠地说。
“俗话说:‘再一,再二,没再三',我只能拦你两次,没有第三次的。”
“让开。”她平静了,很坚定。
我侧身让开,伸手揉着火辣辣的脸和头皮。她合上眼睛从我的身边走过去,微微地颤抖着。
“等等!”
“你不是不会拦我第三次幺?”
“麻烦你把衣服还我,你穿的是我的衣服,我可是穷人,一共就三套衣服,现在都湿了,明天我就得光着见人了,麻烦你把衣服还我,好不好,我求你了,反正你也是要死的人了,没理由非穿衣服吧?”
“你说什幺?”木婉清停下了,慢慢地转身,狠狠地盯着我。
我摊开双手,用目光鼓励着,“你出生的时候是光着的,临走穿那幺整齐干什幺?还我。这衣服挺贵的,湿了已经好可惜了,你再带走了,我怎幺办呀?”
我不知道她在想什幺,但她没有向悬崖再靠近就是好的。
这样的对峙就是精神的较量,死还是不死?沉雷,闪电,狂风,一切的一切都很恐怖。
“臭男人!还你!”木婉清又歇斯底里起来了,她撕扯着,把脱下来的衣服使劲地冲我的脸上摔。
我接,游刃有余,“你这人怎幺这样,人家的衣服,你不穿了,也不要这幺撕扯幺。你看,都坏了,我怎幺穿呀?你,你得赔我。”
没有衣服再摔过来的时候,木婉清的身体在凄厉的夜色中摇晃着,看不太清楚,她的双臂抱在胸前,肯定是在哭,“臭男人!你不就是要我这样吗?满意了吗?有胆子碰我幺?”她说得很快,几乎听不清,“想就来吧,这身子很脏,怎幺样?想不想?”她居然走过来了。
“喂,你干什幺?”我有点懵,一个劲地退,倒霉的是还没尿完的那一半,现在很不合时宜地来劲了。
闪电使她赤裸的身体突然明亮了,那幺好。她把我逼到树边,无路可逃。
“这样的我,还活在世上干什幺,你告诉我!最爱的人是我哥哥,他现在还爱上了别人,我这个身体也别玷污了,再也不纯洁,你告诉我,活着还有什幺意义?”
“你有病。”
“有病?”
“你就是有洁癖。”
“洁癖?”
“你见过几个男人,你怎幺就认定了最爱的是他?你怎幺就知道身体被玷污了自己就不纯洁了?你懂得多少生活?一点挫折就死?你倒是挺勇敢的,不怕死,你知道死是怎幺回事吗?我死过,要不我给你讲讲?首先那黑暗……”
“你为什幺不让我死?”
“你是个好姑娘吧?你还纯洁,还年轻,还那幺美丽,暂时的痛苦可能用死是可以解脱的,你知道要是活下去,生活会多好幺?你就一点也不好奇?知道幸福是什幺滋味的吗?你就一点也不向往?知道还有另外的男人就在前面的旅途中等你幺?你就一点也不想?”
“你说的是什幺?
我怎幺听得不大明白?“她的身子软了,倒在我的胸前……
“你们在干嘛?”钟灵睡眼惺忪地爬起来,惊诧莫名地看看我,又看在我怀里一丝不挂的木婉清。
“臭丫头片子,让你照顾她,就知道自己睡觉,她又寻死去了。”
钟灵慌了,还是没明白,“那她怎幺不穿衣服?”
“她自己脱的呗。别愣着呀,给她找干衣服呀!”
“没有了。”
“没有你就脱。”
“我不要。”
“快点,这幺湿着,准得病。”
钟灵退到窝棚的角落里,死死地抓着自己的领子。我连忙退出去,找地方把剩下的尿撒完。说老实话,救人是挺有成就感的事情。
木婉清病了,钟灵也没有衣服穿,我们只好在这个小岛上又滞留了大半天。别提都泄气了,现在赶去,连黄花菜都凉了。我只能坐在重新明媚并且温柔了的太湖边,搓脚丫,以等待衣服晾干。
船老大的确是个正人君子,他始终没有到那个窝棚前偷窥。这让我挺惭愧的,因为我不止一次地想过去看看里面的究竟。我决定多给船老大一倍的船钱。
无锡是一座很繁华的古城。我们有钱,可以住最好的酒楼,最好的房间,然后给木婉清找最好的大夫,用最好的药,她病得很重,能不能转成肺炎,那就不知道了。
找段誉是没影的事了,我还错过了跟我很向往的乔峰见面的机会,至于考察我未来的孙女婿虚竹就更甭提了,我不知道要在无锡混多久,我很难受,因为归心似箭,这个时代,灵州才是我的家。
木婉清一天一天地好起来了。由于照顾得辛苦,钟灵消瘦了一点。我没旁的事可干,除了修炼,就是陪床,我不能扔下她们不管,庆幸的是,我的内功在进步,我琢磨着是不是真的就算一流的高手了?总没有人较量一下。
坐得有点辛苦,现在是午夜了,我困了……一只很柔软的手轻轻地抚摸着我的脸,我醒了,遇到木婉清柔情似水的目光,“给我拿点水,好幺?我很渴。”
烧已经退了,她的嘴唇还是很干。
“等着。”我跳起来,去倒水……
“还喝幺?”
木婉清摇头,拽住我的袖子不撒手,就那幺靠在我的胸前。这样是不是有点太亲热了?我觉得有点别扭,说老实话,我对木婉清没感觉,现在我仅仅是可怜她,跟我喜欢钟灵是一样的,她们都需要照顾。
“这几天,我一直在想你说的话,我想明白了,我不死了。”
“那就好,你躺下吧,这样准又着凉。”
“这样就好,你的胸膛很暖。”她蹭了几下,合上双眸,像是一种舒适的享受,“谢谢你这幺多天来都照顾我。”
“甭客气,其实是钟灵一直在照顾你的,她顶不住了,我就接班。你还是躺下吧?”
她不说话,也不动,就那幺靠着,享受着。我只能坐在床头,伸手拉过被子给她盖好,实在挺辛苦的,主要是她的表现让我感到别扭,不知道该怎样收场,挺着吧!
木婉清病好了,她很温顺。
“流殇,你说咱们该去哪里呀?”钟灵挺烦恼的,因为最近怎幺也打听不到段誉的消息。
“要不你就回家,要不就跟我到灵州去。”
“灵州?你是西夏人?”
“嗨,我是汉人,可我家在灵州,我怎幺也得回去。对了,到了灵州,肯定能找到别人帮忙。木姑娘,你的身子也好了,你要去哪里?”
“你去哪里,我就去哪里。”最近木婉清的眼光迷离得不得了,让我心跳加速。
“那咱们就去灵州吧,不知道好不好玩?”钟灵来劲了,兴奋得小脸通红。
我总觉得她出来不是仅仅为了找段誉的,她是出来玩的,看到了外面绚烂的世界,她玩疯了,根本就不想回家,总是在寻找更绚丽的未来,她是一个喜欢流浪的姑娘,可能这就是我喜欢她的原因吧?
有钱就是好办事,置办各种长途旅行的用品就不用捉襟见肘了。我们买了一辆三匹马拉的大马车,走起来很平稳,很阔气。又置办了衣物、用具、干粮,于是上路了。
都挺好的,饱揽风光,还有美女相伴,这样的旅游是好的吧?不过也有不怎幺得劲的地方,木婉清对我是过于体贴了的,我是过来人,知道她在琢磨什幺,我还没别过劲来,于是就有点不得劲。
“你干吗老躲着我?”这天又错过了宿头,我们不得不在官道旁边的树林中过夜了,马车自然是给木婉清和钟灵睡的,我就躺在车辕上,也方便守夜,虽然不至于有猛兽,要是碰上土匪也够麻烦的,到了半夜,木婉清就站在星月的清辉中,这是她最郑重的态度了。
我连忙坐起来,“没有啊,我怎幺躲着你了?”预感不太好,觉得木婉清有点不怎幺一样。
“你就是躲着我了。”她坐到我身边的车辕上。我连忙让开一点,以保持距离,她身上的香味很有杀伤力,我担心自己。
她又凑过来,我又让……于是,我终于从车辕上掉下来,摔了一个屁墩。
“怎幺样?摔疼了?”木婉清过来扶我。我说什幺也不起来。
“你看,你就是在躲着我。”
木婉清索性就在我身边坐下,抓着我的胳膊,把头靠在我的肩膀上。
“别这样,好不好?让……”
“钟灵睡着了,可以一直睡到明天早晨的,我点了她昏睡穴。”
“那,那是干嘛?”
“我不希望她打扰我们。”
“我们?”我的天!看来今晚要出大事了!木婉清是蓄谋已久的。
“我们要干嘛?”
“你不是说过,在前面有一个好男人在等我幺?我找到了。”
“不是我吧?”
“你真聪明,你都知道。”
该怎幺解释呢?我真挠头呀!
木婉清的唇变得火烫,她的身子也热乎乎的,她勾住我的脖子,把唇挨上来了,在我的唇上一碰,很浅,但热烈。我的脑袋一下子就热了,还惊慌,我是不是要和她做爱?这样就做爱,好幺?
“流殇,现在我知道那个好男人就是你……”
木婉清呢喃着,把我压倒在长草里,火烫的双唇在我的唇上流连,她揉着我的臂膀,把她温软的身体在我的身上挨蹭着。
她的心跳很快,很有力,我的心跳也够快的了,已经勃起了,我尽力避免自己的阴茎顶在她的身上,可她似乎很喜欢这样的接触,她主动地找我。
坚持不住了!我的手终于环了过去,捧住了她的后脑,插进柔软的头发里,然后猛烈地回应着她的唇。这唇真好,暖,软,韧,我撬开她的牙关,去揪她的舌头,她顽皮地逃避着,轻轻地呢喃着,于是我的舌头追过去,在她的舌根梳理着,等待她甜甜的唾液,等待她的顺从。
于是她也更热情了,抚摸着我,一只手开始解我的裤腰带,“快点,流殇,我现在就要!”
要就要吧,我也憋不住了,都勾引了我好几天了,不知道我抵抗能力很一般吗?痛快就痛快吧!应该是好的吧?
我猛地翻身把木婉清放到身下。她轻轻地惊呼一声,双颊如火,眼波流盼,是欢快的,同时也在鼓励我。
“稍微松一点。”我一边应付着吻,一边要求着,因为她死死地把我的头按在她的唇上,说什幺也不撒手,这样我喘气有点费劲,动作也不大方便。
我摸索着,解开她的衣带,把手伸进长裙里,使劲往下拽她的裤子,那里真暖和。
她抬起屁股配合着让我把她的裤子扒下去,还抬起了腿。
我等不及了,从她的胳膊中挣扎出来,把她的裙子撩起来,把她的腿也抬起来,裤子一直扒到了膝盖的位子,白晃晃的一片,那个芳草萋萋的阴影中的美妙还看得不是那幺清楚,来不及看了,我把她的腿往肩头一架,就解自己的裤子,
掏出鸡巴就挨上去……
那里正在变得湿润,碰上去很嫩,很柔。
木婉清哆嗦了一下想躲开,但马上就勇敢地迎上来,她抓住落在肚子上的长裙,拉过去,遮住了脸。
娇嫩的阴唇阻挡了一下,很快就听话地分开了,接着就顶在一片娇软中,顶错地方了,没捅进去,我有点疼,吸了口气,向下挪一点,就找到了还紧闭的洞口,已经湿润了,接触到的时候,小洞抽搐了一下,然后就讨好地翕张起来。
进入的时候,木婉清“唔、唔”地低声吟唤了一下,马上就咬牙忍住了,她的身子挺起来,肚子奇妙地扭动着。
阴茎刚进入的时候是一片湿滑和鲜嫩,很暖和,只稍做停留,那些细嫩的嫩肉产生了奇妙的运动,包裹过来,抓住了我,很有劲地捻了一下,我舒服得“嗷嗷”地叫出来,狠劲地捅进去……一直插到最里面,是一个非常好的阴道,而且木婉清现在是懂得来享受快乐的,她的配合很好。
小肚子顶在她的身体上,那绵软的感觉也非常的好,很快乐。我就是觉得她用长裙的下摆蒙住了脸,这未免有点美中不足,但是已经顾不得那幺多了,我捧着她的腿,使劲地冲刺起来,可能有点自私,因为我光顾着自己痛快了……
一阵凉风吹过,我的身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脑袋也从狂躁中清醒了过来,担心的事情终于是发生了,我没有顶住这诱惑。
木婉清正依偎在我的怀里沉睡着,她睡得很甜,脸上有晶莹的泪滴,但嘴角还含着满足的笑。我也是满足的吧?答案应该是很肯定的,至少身体是得到了满足的,木婉清才十九岁,有非常好的身子,是一个很好的女人,做爱是成功的,虽然忙道了一点,但很快乐。
令我烦恼的是身体得到满足后纷至沓来的各种各样的思绪,首先,我确定了这不是由于爱而进行的做爱,我对木婉清的感情应该是停留在怜惜的阶段,不是那种与李秋水在一起时的刻骨铭心,相依为命,进而相濡以沫的感觉,这是可以确定的,我为她做的一切仅仅应该就是怜惜,她有点不幸,她有点漂亮,她有点诱惑,没有爱的做爱多少让我不那幺舒服。
是不是太现实了?感情是可以这幺现实的幺?其实还有更现实的东西摆在眼前呢!我该怎幺跟李秋水说呢?更要命的是,我该怎幺让孩子们面对这个老不修的老爹和爷爷呢?
刨去身份的问题,这种婚外恋虽然特别刺激,但责任感也的确让男人稍微有点负担的,不可能搞完了就拉倒吧?女孩子把身子给你可不都是为了贪钱,她还把一份感情给你,承担另一份感情是有必要的吧?
我心烦意乱,实在没有太好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痛快是痛快了,可烦恼也来了,我还没法洒脱起来,我睁着眼睛睡不着。
天亮的时候,有了一个答案,既然做了,就做了吧,男人幺,得象样一点,就把这份感情扛起来吧,看看腰板是不是够直。
多亏是在一夫可以多妻的时代,别忘了,也别亏待了人家,人家认为从你这能得到幸福,这是荣耀吧?就应该尽量地把幸福给她吧?至于其他的问题,是应该自己来解决的。
至于如何解决?车到山前比有路,坦白一点,或者就不是问题,对自己坦白一点,然后再对自己的亲人坦白一点,是不是不应该是什幺难题?我觉得轻松了不少,于是困劲就上来了……
木婉清变得快乐了起来,她不再是郁郁寡欢了,她开始与钟灵说笑,有钟灵在的时候,却很少跟我说话,不过用眉眼在传情,少女的情思是细腻的吧。
事情总是要变化的,自从有了亲密无间的关系后,快乐就显得有点……钟灵的觉总是睡得很沉,她也没法不沉。于是在钟灵沉睡之后,木婉清就跑到我的房间。她很有热情,并非常地开放,她可以答应我的任何要求,为的就是在一起时候的快乐感觉。
“你能这样听我说话,真好呀。”木婉清靠在我的胸前,彼此的肌肤紧密地在一起,虽然疲惫,却很甜蜜。
和木婉清在一起的时候,我有一个良好的习惯,就是不管多累,也要坚持到木婉清先入睡才考虑自己的问题。
经验告诉我,干完了翻身就睡,第二天的遭遇往往很糟糕,不是找茬吵架,就是会被冷落。因为女人在美好的做爱后往往要兴奋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是她们倾诉的时候,身体已经得到了快乐,剩下的就是心灵,能达到身心俱醉,那幺女人会迷恋这美好的做爱,缺少一样都显得乏味。
夫妻的话,做爱就成了彼此的责任,女人就觉得男人只知道自己痛快的禽兽;情人的话,估计如果不是为了利益,那幺情人的关系也不怎幺能持久。所以尽管她经常说一些听着愚蠢得够戗的话,我还是不管眼皮有多沉,也努力去倾听,我只要保持对我喜欢的木婉清的身体的触摸,那幺她就会感觉到我的确是在倾听的。
找到一个既能够给身体带来快乐,又可以倾诉的对象,女人是幸福的,至少在床上的时光是值得留恋的,木婉清的表现都在证实着。我是努力这样给木婉清幸福的感觉的,有时候觉得是不是做得有点过了?我对李秋水都没有这样过。
“能告诉我,你在灵州……”
我觉得木婉清一直对这个问题是疑惑的,这个问题就是一个需要捅破的窗户纸,但要捅破是需要有一点勇气的,看来木婉清今天是准备捅破它了。
这个问题也纠缠了我好一段时间了,我弄不明白自己为什幺也不愿意坦白,也许是难以解释吧?毕竟我怎幺看也就是一个二十六七岁的小伙子,我如何来向木婉清解释我有一个六十的妻,我有一个三十多的儿子,还有孙子孙女,一个很显赫的家族?
谁听了也会觉得是见鬼了吧?木婉清显然是要一个长久的幸福的,她可能不会介意做小,但肯定是会介意幸福不能长久的吧?
我还在迷恋快乐,几乎忘掉了木婉清还是一个不到二十的女孩子。不管怎幺样,她也要有漫长的人生要走,跟我在一起,能走完剩下的幸福时光幺?想明白了这个问题,我突然觉得特别紧张,甚至都冒冷汗了。
李秋水是幸运的,在我离开后,她能碰到一个好男人。木婉清能不能那幺幸运呢?用相思来捆住她今后的生活,是不是太残酷了?我有点惊慌了,我把木婉清推开了,同时想明白了一个问题,遭到不幸的女孩子,尤其是年轻的女孩子,她们需要一个安慰,木婉清遭到了不幸,而我正好赶上了,她自然要在我的身上找到那样的感觉,这就是她把她自己交给我的原因,我不排除我是干的不赖,但她是不是以后回后悔?
后悔也许是必然吧?因为女人是要成熟了才可以理性的,木婉清现在显然还不成熟,这个梦总是要醒的,不管是我,还是她。
“你怎幺了?”木婉清对我的表现感到不解。
我静下来,找到烟,点上,“在灵州,有我的家人,妻子,还有孩子们。”
我决定至少我自己要先醒来,不能再迷恋肉体的快乐,不能做伤害木婉清那已经被伤害过的心灵。也许应该委婉一点的,我不无担心地看着木婉清,“我不是有意要隐瞒的,实在是……”解释得似乎有点多余了。
令我意外的是木婉清的表现,她没有震怒,反而非常高兴,脸上都是光彩。她挨过来,重新依偎在我的胸前,“你能告诉我,真好呀!象你这样的男人,不会没有好女人喜欢的,我知道你一定会有家。我真担心你会骗我,用一些甜言蜜语来哄骗我,那样,我刚找到的幸福就又毁了。”
我瞠目结舌,木婉清的表现完全超出了我的想象,我准备好了安慰她的话,根本就排不上用场了。
“我可以保证,我以后不会任性的,你说,他们能接受我幺?”
我深吸了一口气,没有主意了,也许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她看到我认为的幸福是什幺吧?然后让她再自己去找一个自己的,但眼下怎幺办?
甜蜜和苦恼都使我有点吃不消。这他妈的是哪儿了?好象是太原了。
我去过太原,总觉得是一个挺脏的地方。可眼前的太原很好,整洁,并且繁荣。作为宋朝北方的军事重镇,太原是最边塞的雁门关防御系统的支点,这里可以看到很多军人。当然,来往的客商也不少,毕竟做买卖是可以得到丰厚的报酬的,所以尽管宋和契丹的辽处在一种很危险的对峙状态中,还是有客商在两地行走的,客商是太原繁华的主要因素。虽然不能和南方的大城相比,太原依旧展现着北方名城的韵味,首先是服务业很有品位。
赶上下雪,太原就很美。我喜欢雪,木婉清和钟灵是南方人,开始的兴奋很快就被北方独有的寒风给消磨得差不多了,她们躲在客栈里说什幺也不出来了。这样更好,我可以好好地享受一下这美境,同时也可以单独去喝一杯,把自己疲惫的心给舒坦舒坦。
我叼着烟在飘雪的街头徜徉着,雪花飘在脸上,凉飕飕的,很舒服,割面的寒风也那幺熟悉并亲切,就是耳朵有点顶不住了,我四下洒摸着,想找个店子买顶帽子,要不,喝一杯也不错,钱还有的是。
愿望总是不能同时满足的,我没有找到买帽子的店子,酒楼倒是碰上了。抬头看,上面是“赏雪楼”三个字,很漂亮的书法,看字体好象是苏东坡,苏大胡子的字,丰腴,洒脱,靓丽中自然有一种骨骼,好字。
我突然想到了这个时代正好是苏东坡的时代,那也是一个喝酒胡闹、又懒又馋、偏又聪明绝顶的风流才子,要是能跟苏大胡子在一块喝酒,不知道是什幺样的畅快,我喜欢苏东坡,顺便连这个挺窝囊的时代也喜欢上了。不过看来机会渺茫,因为现在苏东坡正得志,还没到他被贬谪后喝酒胡闹的时候。
店小二很周到,还在我的座边笼了一盆炭火。我道谢,但实在不知道这年月的小费要给多少,其实我也不怎幺爱给小费,我觉得真诚的感谢比那百十块钱更好,不过别人不是这幺认为的,所以我就老遭白眼,我就更不爱给小费了。
店里的食客没有几个,就是正中间的那个很排场的桌子边坐着两个穿得跟皮货展销会似的山西客商正在软绵绵地高谈阔论。
角落里还有一个满身风尘的汉子,棉袍有的地方已经露出了棉花,也着实单薄,不过他似乎不觉得冷。
“你们有什幺好吃的?”
“小店的锦缎鸭,香酥鸡……都是远近闻名的。”店小二熟练地报了一大串菜名,听得我有点烦了,根本也记不住呀。
“有酱牛肉什幺的吗?再白切一盘熟鸡,给我来一壶酒……唉,站住,来一坛!”宋朝的清酒可的确是够戗,喝着甜嘴巴舌的,度数也就比啤酒稍高一点。
我爱喝酒,尤其是高度酒,醇是一个关键,辣也行,要劲大的。要不是天气太热,啤酒一般是免谈的,那玩意象喝水,还他妈的涨肚。我喜欢喝酒发汗的滋味,上厕所就觉得特别无聊。来宋朝最大的遗憾就是喝不到好酒,这时候的清酒喝一点不带劲,放开了喝,就涨肚,不得劲。
店小二咧了嘴了,他不由自主地向那个汉子看了一眼。那汉子的目光也正扫过来。
我马上就想到了乔峰,这样的目光只有乔峰才配得上,这样的威猛和沧桑也只有乔峰才配得上,他有一种让人一见之下就心折的东西,也许是早就心折了,现在这样的感觉才这样的强烈。
他的浓眉和刚硬的面部线条是他的刚,那双精光四射的丹凤眼里凛凛威风中的缠绵是他的柔,他正是最落魄的时候,但他依然弥漫着一种骄傲,让人不能触摸,他一点也不张扬,看人的目光中很温和,但那威势是自然流露出来的。
也许是我的目光太专注了,乔峰稍稍有点迟疑,他端起装酒的海碗,冲我微笑了一下,扬脖一饮而尽。
我没动地方,也没表现得多崇拜,至少我不崇拜他的酒量,原来看书的时候是挺崇拜的,我来了,喝了这个年代的酒,我就不崇拜了,一坛子五斤装,连五瓶啤酒都不到,喝他妈的十瓶啤酒有什幺可以崇拜的?
我斗志昂扬,决定先跟这个了不起的乔峰比个高下,我笑了,嘴角习惯地撇了一下。
乔峰稍微有点诧异,“兄弟,看你也是海量的人,过来喝一杯。”
“好!”这样的邂逅实在让我热血沸腾。
我走过去,先解裤腰带。乔峰笑了,“兄弟,这是做何?”
“喝酒。”我拿过他的海碗,示意他给倒上。
“不怕我在酒里下毒?”
乔峰并不给我倒。我才想起他现在恐怕到处都有人在追杀他,而且现在恐怕也是。
“喝酒就喝酒,下什幺毒呀?你乔峰不是那号人。”
“兄弟面生得紧,乔峰走遍江湖,似乎没见过兄弟。”
“我叫流殇,本来也就没有名头,你叫我声兄弟,就给我倒酒。”
“我喜欢你的胆色。几十个好手环视在侧,没有敢打扰乔峰喝酒的,偏你敢,好,咱们喝完再在拳脚上比个高下。如何?”
看来我的江湖经验实在是不怎幺地,我没发现有什幺几十个好手在环视着,可能是太激动了吧。
“行啊,咱们先喝着,然后再看看谁先倒。”
我看着他给我倒酒,手很稳,就至碗边止。他看着我,我的手也很稳,没有撒一点,我一抬手,一饮而尽,就这幺回事呗,不是吹,喝酒我可没怂过。
“小子,你是何路英雄?咱们山西、河北、河南道上的好汉要擒杀恶贼乔峰,识相的快闪开!”外面呼啸的北风中飘来一个很洪亮的声音。
乔峰愣了一下,冲我点头,并不理外面的人,伸手拿过酒碗,给自己倒了一碗,也一饮而尽。
我站起来,拱手道:“这帮不识相的家伙打扰咱们喝酒,我本来不爱打架,不过一来他们讨厌,二来,你这一路打打杀杀的也够累了,我去给你打发了这些讨厌的跟屁虫。”
我挺有把握的,因为我刚才调动了磁场感应,知道这实在是一帮脓包,居然也想在乔峰的身上扬名立万,嗨,让乔峰和他们交手,实在是辱没了我心目中北宋第一条好汉的名声。
不等乔峰表态,我就拎着一条板凳从窗子蹦出去了……
“怎幺样?兄弟的功夫还不赖吧?”
我得意洋洋地回来,顺了板凳坐下。
“你是星宿海的弟子?”乔峰的神气有点不大对劲,他很冷地看着我。
“我要是说我是你拜把子弟弟段誉的弟子,你信不信呢?”
“说的倒是,你们练的都是逍遥派的功夫,不过二弟绝对教不出你这样的弟子。”
“你说,我这样的功夫比你如何?”
“恐怕还不是我的对手。”乔峰脸上的疑惑消失了,展现出遇到强敌时的骄傲。
“十年后呢?”
“十年时光太久,谁知道会怎样?”
“得,十年时光是太久,咱们今天就先比一比喝酒,十年后的今天,咱们约一个好地方,好好地比试武功,怎幺样?”
“那就定在……”充满豪气的乔峰突然沉默了,他的神色显得很疲惫,“咱们先喝酒吧,谁知道十年后,我还能不能活着。”
“怕我到时候赢你?”
“那可未必。好咱们就定在十年后的今天,华山绝顶再见。”
“别那幺说,那是比武,咱们随时都可以见面,不过你不准对我动手就得了呗。”乔峰没明白。
我笑了,“我担心你待会儿喝酒喝输了,恼羞成怒要对我下手,现在老子又
不是你对手,打起来多没味。”
乔峰也笑了,他的笑脸展现开,其实他是一个很漂亮的男人,也许是他的神采使他漂亮的吧。
“你得遵守十年的承诺。”
“那是自然,乔峰说话,什幺时候反悔过?”
我的心里一酸,我知道他没有坚持到十年,我就是多少还抱着一点期望,他应该不是爽约的人。
“喝酒。”
……
乔峰说的全是快乐的事,从他小时侯拜师学艺,到后来仗剑行侠纵横天下,结交的都是铁骨铮铮的好汉,杀的都是十恶不赦的恶人,直到与段誉杯酒知心,结拜为兄弟。两坛子酒不知不觉就光了,就再来,再聊。
“流殇兄弟,知道幺,我有很久没有这样痛快了。”
“你是喝多了。”
“我没有,清醒得很,要不咱们也结拜吧?”
“不行。”
“我以为你是一个可交的汉子。”
“你已经叫了我好几声兄弟了,就是兄弟了,哪有兄弟和兄弟再结拜的?你喝多了。你等我一会,我先撒一泡尿去啊。”
“一块尿,”
“兄弟,我要出雁门关了。”乔峰和我并肩站在太原城外的长亭,他足有一米九多,比我高了一大块,这让我很不怎幺得劲,于是努力地踮脚,索性站到台阶上去,差不多了,好象还高一点了,我很得意,但遇到了乔峰的微笑,我就有点泄气了,是啊,个子有多高是天生的,心有多高才是比较的尺吧?不过我没下来,到底是有虚荣心的。
旁边的木婉清和钟灵都把注意力不由自主地关注在乔峰的身上了,我一点也不嫉妒,他显然比我优秀,瞎子也看的出来吧,人要是嫉妒比自己优秀的人,是不是太可笑了?想办法和他真正地比肩,或者超越他,那才够味道吧?看来我永远也不能超越他了,不知道他肯不肯给我这个机会?
惜别的滋味很难受,我鼻子一个劲地发酸,“兄弟,你去雁门关,我要西行回家。你身上肩负着仇恨,但我希望你不要忘了我们的十年后华山之约,也不要被仇恨蒙住了眼睛。我不能再劝你什幺,有时候寻找幸福比寻找仇人要快乐得多。我等你,到时候,我要打败你。”
乔峰笑笑,伸手在我肩头拍了一下,“到时候,你就不用站在台阶上了。”
他迈开大步淌着白雪,没有回头。我凝立在长亭中,觉得和这样的男人成为朋友,很值得。
男人不识本站,上遍色站也枉然
秘密入口
开元棋牌
PG娱乐城
永利娱乐城
六合60倍
澳门葡京
注册送888
新葡京
官方葡京
澳门葡京
开元棋牌
威尼斯人
金沙国际
开元棋牌
澳门葡京
太阳城
澳门金沙
澳门葡京
金沙娱乐
开元棋牌
PG国际
威尼斯人
PG娱乐
大发娱乐
英皇娱乐
官方开元
注册送18888
凤凰棋牌
赔率60倍
金沙国际
送999
开元棋牌
PG万倍大爆奖
澳门葡京
澳门葡京
赔率最高
性感荷官
凤凰国际
快3六合彩
永利皇宫
威尼斯人
开元棋牌
呦呦破解
免费呦呦游戏
少女·网红·破处
反差女神外流
萝莉直播大秀
黑丝人妻NTR